让周俭民获奖的,是他与柴继杰合作发现的一种寡聚的抗病蛋白:抗病小体。他觉得抗病小体有着无与伦比的美,其结构令人惊叹,“像一个风火轮,也像一朵紫荆花”。
编者按:现在,让我们把聚光灯对准中国基础学科的研究者数学家、化学家或者人类基因的研究者。
我们希望能够抛开科技报道对巨头公司和创始人个人生活事无巨细的关注,回归到科研最基本的单元:科研者。
这些研究者是谁?在干什么?在担忧什么?面临什么?他们所做的事情,在世界范围内又处在什么样的序列?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张铃飞机刚刚落地,植物免疫学家周俭民就收到一堆短信,还没来得及反应,新电话进来了,号码显示为“管坤良”。
管坤良是国际知名生物化学和细胞生物学家,刚刚回国任教,并担任未来科学大奖科学委员会2023轮值主席。管坤良告诉周俭民:你是今年“未来科学大奖生命科学奖”获奖者!
消息很突然,机舱里都是乘客,一时间,这个在实验室里和植物打了30多年交道的科学家有些混乱,不知该如何做表情。
未来科学大奖有“中国的诺贝尔奖”之誉,奖励给有前瞻性、开创性的基础科学研究。2023年,生命科学奖由周俭民与结构生物学家柴继杰分享,奖励他们在发现抗病小体并阐明其结构和在抗植物病虫害中的功能做出的开创性工作。
我们做了一些比较令自己满意的工作,对未来农业的一些重要问题,比如病虫害的防控问题,可能起到比较积极的作用。
热闹结束了,周俭民回到了他的实验室。办公室不大,书本堆在桌上,有些杂乱,他穿着一件《植物学报》发给编委的墨蓝色POLO衫,在这里伏案工作。
让周俭民获奖的,是他与柴继杰合作发现的一种寡聚的抗病蛋白:抗病小体。他觉得抗病小体有着无与伦比的美,其结构令人惊叹,“像一个风火轮,也像一朵紫荆花”。
他打开电脑,向经济观察报展示一个会标:一段双螺旋DNA充当锚杆,左右镶嵌着两片叶子,一个五瓣花朵高高开在铁锚上。
这是2023年国际分子植物与微生物互作学会双年会(IS-MPMI2023)的会标,主题是“通过植物微生物研究保护我们的星球”,领域内顶尖科学家汇集于此。

历史上,植物病害的暴发对人类文明产生过重大影响。1845年到1850年间,爱尔兰大饥荒使爱尔兰人口锐减了四分之一,起因就是晚疫病的卵菌造成的马铃薯腐烂。现在,全球有高达40%的农作物产量因植物病虫害而损失,每年给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超过3000亿美元。
100多年前,有英国学者发现了植物的抗病基因,也就是植物自身具有抵抗病虫害的能力。上世纪40年代,美国植物病理学家弗洛尔(HaroldFlor)提出著名的“基因对基因”假说,认为植物存在一组抗病基因,可以与病原微生物的致病基因匹配,从而引发植物的免疫反应。90年代初,植物抗性基因的克隆从分子上佐证了这一假说。
那么,植物的免疫系统如何对抗病虫害?如何在分子的水平行使生物学功能去对抗病虫害?科学家们此后二十多年的努力,都未解密抗病蛋白的工作原理。
周俭民打了个比方,抗病基因像是调动免疫系统的总指挥,它可以调动千军万马去抵抗病原,但人类并不知道它具体发了什么命令。
常规的研究手段已经穷尽,结构生物学手段或许大有用武之地,这是周俭民和柴继杰的共识。长达19年的时间里,他们精诚合作,最终发现了由免疫受体激活后形成的抗病小体,并解析了其结构和功能。
他们发现,抗病小体是由免疫受体蛋白在识别病原体效应子后形成的多组分复合体,这种复合体通过形成钙离子通道引起植物免疫反应,从而保护植物免受感染。这是近年来植物免疫研究领域的最重大的进展之一。
国际植物抗病研究权威科学家Jeffery Dangl 和Jonathan Jones 在Science发表了专文评述:“首个抗病小体的发现为植物如何控制细胞死亡和免疫提供了线索”、“澄清了对NLR 蛋白功能的诸多猜测”和“这些重要发现大大加深了我们对植物先天免疫机制的认识”。
从基础科学研究到应用真正落地,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可以确定的是,因为这个发现,未来人类将找到更好的植物病害控制方法,更好地防控农作物病虫害。
2003年一个雪天,周俭民、柴继杰都来到了美国纽黑文国际机场附近的一家酒店,几个有名的科学家也在这里:国际著名生物学家吴瑞,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下称“北生所”)共同所长王晓东、邓兴旺。
这一年,作为“中国科技体制改革试验田”的北生所筹建,无行政级别,无事业编制,科学家自主确定研究方向,也可以不为经费发愁,一批优秀的年轻学者闻声而来。
和邓兴旺、吴瑞谈过之后,在美国已有教职的周俭民决定回国。2004年,他正式加入北生所,成为首批“PI”(独立实验室负责人)之一。
北生所远在昌平,彼时周围都是村庄,但周俭民很喜欢这里。他和柴继杰的实验室都在二楼,面对着面,两人常常交流,偶尔抽支烟。柴继杰是结构生物学专家,刚好也对植物抗病感兴趣,几根烟的功夫,双方一拍即合。
2007年,在周俭民的配合下,柴继杰小试牛刀,解析了第一个弗洛尔抗病蛋白的复合物结构。虽然这只是一个非典型抗病蛋白,但这项工作让二人得以提出抗病蛋白识别病原的新模型:“诱饵模型”。他们认为,某种“诱饵”蛋白会将细菌毒性蛋白引入“空城”,一旦“诱饵”蛋白被破坏,抗病蛋白就会迅速激活,指挥被感染的细胞与细菌“同归于尽”,阻止病原体扩散,从而保证周围组织的正常生长。
历经10年不断尝试,柴继杰实验室发现经典弗洛尔抗病蛋白ZAR1可能是理想研究对象。同期,周俭民实验室对诱饵模型反复求证,并于2015年利用诱饵模型成功发现了ZAR1蛋白复合物的组分以及相关生化机制,加速了ZAR1蛋白复合物的结构生物学研究。
长时间困扰植物免疫领域的一个问题是,抗病蛋白是否形成寡聚体?几乎每个月,两个实验室都要一起开会讨论,寻找线年,两个实验室分别从植物细胞和体外重组蛋白实验获得了ZAR1蛋白寡聚的证据。最为重要的是,柴继杰实验室成功地在体外重组了ZAR1寡聚体,并解析了其结构。他们把寡聚的抗病蛋白称为“抗病小体”。这是抗病小体在国际上首次被发现。
ZAR1抗病小体的独特结构,暗示它很可能在细胞膜上成孔。此后,生化、电生理、细胞生物学和抗病功能验证证实了ZAR1抗病小体的确在细胞膜上形成孔道,发挥钙离子通道的作用,激活抗病反应,从而保护植物免受感染。随后的遗传学和功能验证完全支持了结构生物学的发现。
文章一经发表,国际植物免疫领域一片欢呼,同行的惊叹溢于言表,将抗病小体的发现和功能解析视为植物先天免疫领域的里程碑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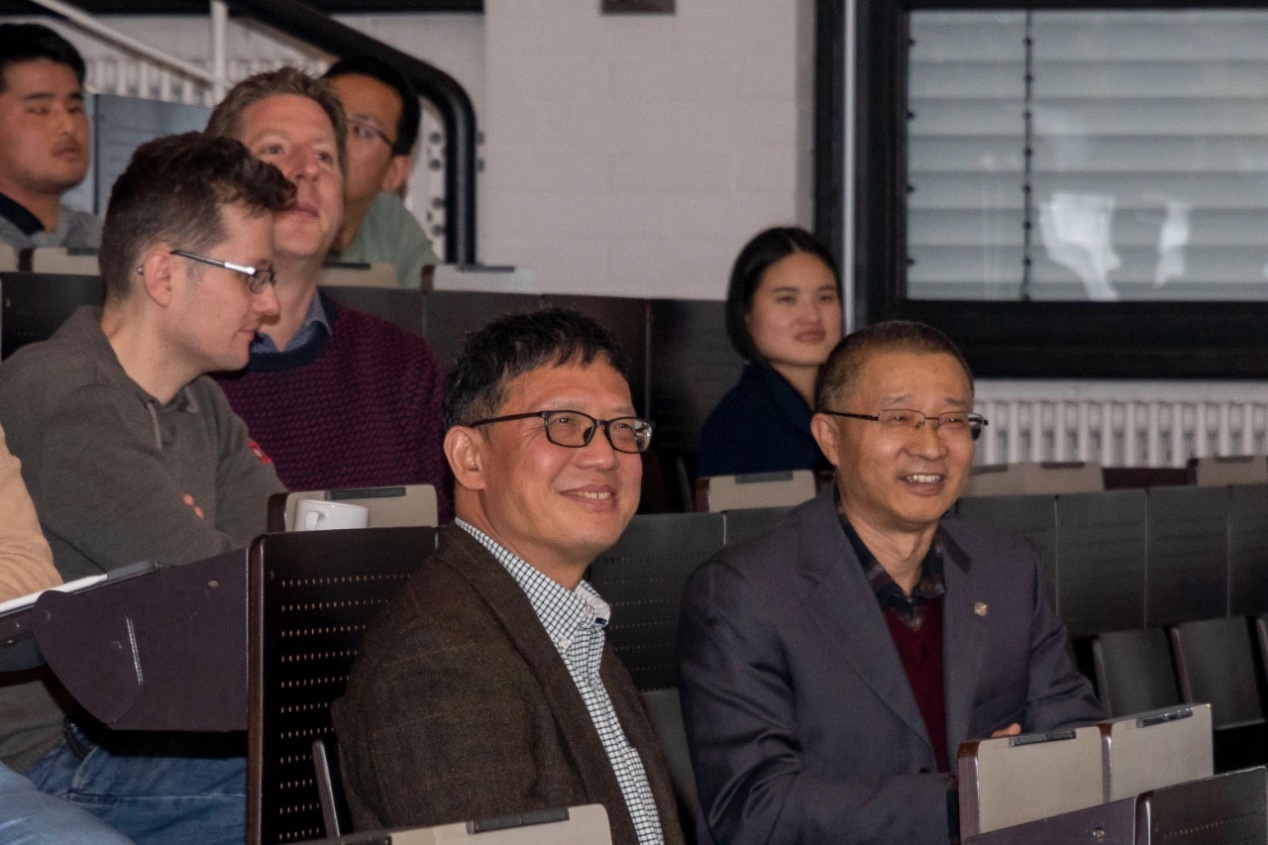
在周俭民眼中,柴继杰这个最重要的合作伙伴生活上像一杯白水,但工作上极为专注,推进速度非常快,“我们整个植物抗病领域,因为他的加入提速了至少5-10年。”
合作卓有成效,又非常愉快。1+12,真正的合作,是有实质性的相互促进。共同的兴趣、互补的专业技能、相互的信任,成为支撑合作的基础。许多年里,两人从没因发文章署名这一类的问题闹过矛盾。把科学问题回答好,这是最重要的。“至于谁的名字放在哪里,不需要特别计较”,周俭民说。
高中时期,周俭民就被生物课堂迷住了。上世纪70年代,普通人对生物学的理解还只是花草鱼虫这样的动植物,但他的老师会讲遗传,有趣极了。
凭着直觉般的喜欢,1980年,16岁的周俭民报考了四川大学生物系遗传专业。这是他唯一违背父母意愿的选择。
80年代的大学校园,黑格尔、诗歌、文学、哲学、量子力学是时尚,专业课反而经常不受欢迎。周俭民不跟风的性格,使其免受干扰。
不易被人左右,这种天性似乎遗传自父亲。父亲是50年代入党的老党员,期间,父亲有自己的判断,他不仅远离,还经常为受到批斗的老同学提供庇护所。
1984年,周俭民考入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宿舍在所里的农场里,不通暖气,北风一来,毛巾冻在铁丝上,回想起来仍觉有趣。下午从实验室回来,他会在晒谷子的场上跟小伙伴们踢上一场足球。
研究生期间,在导师周嘉平的建议下,周俭民去北京农学院(今中国农业大学)旁听了曾士迈院士讲授的《植物免疫》,在那里,周俭民第一次听到了弗洛尔的“基因对基因”假说。
这个假说在周俭民心里埋下一粒种子:植物和微生物,两个活的生物之间,竟在微观层面会相互识别,这太神奇了。
之后,周俭民赴美到普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前夕,植物抗病领域迎来激动人心的时刻,第一批弗洛尔的抗病基因正在被克隆,人们认识到,植物抗病的本质就是先天免疫,免疫系统不仅存在于动物,也存在于植物中。
1994年,博士资格考试时,周俭民的考官之一是格雷格马丁(Greg Martin),他正是最早克隆抗病基因的几位先驱之一。当时,周俭民有收到其他三个非常有名的实验室的offer,相对来说,格雷格马丁是年轻的新教授,植物遗传也是刚兴起的前沿领域,但进入他的实验室开展博士后研究,成为周俭民的不二选择“兴趣和好奇心再次胜出”。
对植物抗病研究的爱,把周俭民正式带到了这个领域。植物与病原微生物间的相互作用是那么奇妙,无穷的生物学问题都蕴含于此,他用两个词来形容这种奇妙流连忘返、叹为观止。

周俭民常跟学生讲,做科研,要把科学问题想在前面,想清楚什么是重要的科学问题,问题的解决能不能影响很多人,能不能改变人们现有的认知。极具科学价值的课题,突破口往往难找,有研究套路的课题,往往很平庸。
这样的课题,一做就是好几年,需要反复试验,寻找线索,有时,学生们难免产生能否做下去的疑虑。一旦看准,周俭民不轻易放弃,哪怕参与课题的学生有一星半点进展,他都会及时肯定、鼓劲。
2007年提出的“诱饵模型”,当时并不被看好,甚至还影响了文章的发表。周俭民团队的另一项重要工作的论文,也长时间不能获得期刊编辑们的青睐。
类似的挫折,带给学生较大冲击。周俭民知道,科学的发现不光要说服自己,还要说服同行,包括那些最权威的同行,没有捷径可走,只能不断地寻找新证据,用事实说话。
十几年过去了,“诱饵模型”早已被验证,当初不被青睐的文章依然频繁地被同行引用。周俭民相信,经过磨砺的科研工作者,会养成保持好奇心、甘于寂寞的品质,“只要做创新的东西,质疑永远会存在”。
父亲今年90岁了,他在无锡农村长大,50年代到成都上地质大学、定居,生下两个儿子。他给小儿子取名“俭民”,希望这个孩子长大后,做个勤俭的老百姓。
父亲会养蚕、包皮蛋、做腌菜、编草筐,周俭民也常和哥哥一起晒腌菜、挑水、洗衣,童年平静而幸福。1996年,父亲去普渡大学看孙子时,闲不住租了一块地种菜,把菜园子料理得极好。和小时候帮着晒腌菜一样,周俭民会到地里帮忙。

父亲开明也讲原则。有一段时期,周俭民成绩变得不太好,父亲告诉他:“没关系,将来你能够养活自己就行。”初升高时,周俭民选了很快能参加工作的中专,父亲出差回来知道,特别生气,赶紧跑去招生办改志愿。周俭民至今感谢父亲的决定。
在普渡大学,周俭民的博导Peter Goldsbrough教授同样宽厚、细致,给学生自由探索的空间。周俭民至今记得,写第一篇科研文章时,导师把文章打印出来,在办公室当着他的面用红笔修改,边改边讲每一处修改的原因。
30年过去了,站在办公桌前的人发生了转换。现在,周俭民也会把第一次写论文的学生叫到跟前,一字一句讲,该怎么写、怎么改,细到每一个标点甚至空格。“就像打通了关窍,从此就知道应该写成什么样了。”2019年加入实验室的博士生郑小娟说。
2017年,还在四川农业大学读研时,郑小娟就被周俭民吸引了。那年,周俭民到成都作报告,关注到了四川的猕猴桃溃疡病,那是全球猕猴桃产业最严重、最难治的病害,一旦发病就会毁园,上百万元投入化为乌有。第二年,周俭民找四川农业大学要了菌株,派人来做采样,郑小娟就联系了他。
现在,周俭民继续深化着抗病小体的研究,同时将一半精力投入到农业应用研究中,研究水稻、油菜、猕猴桃如何抗虫害。他希望未来人类能够去设计植物抗病基因,进一步减少农药的使用。
2012年,周俭民加入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少有人知的是,最初几年他研究经费并不充裕, “比较穷困”。一位朋友来看他,给他带来这两幅字。
禅悦为食,这是一句佛教用语,意谓僧人把从禅定所得到的喜悦,作为滋养身心的饮食,周俭民喜欢这句话。在科学研究中,他希望“更重视精神的愉悦,不因缺经费跳脚”,像植物那样淡定。
从实验论文中暂时抬起头,穿过实验室和养满植物的小温室,周俭民来到阳台上整理实验思路、消化刚刚阅读的文献。向北望去,目之所及满是绿意,万物在悄悄生长。
